扬州城的秋风里飘荡着青槐的香气,徐敬业站在大明寺的台阶上,望着十万甲士的寒光刺破长空。
这位英国公的长孙腰间,祖父李勣征战高句丽时佩戴的龙纹宝剑正在鞘中低鸣。684年九月的这场豪赌,既是李唐宗室最后的怒吼,也是门阀士族对女主临朝的拼死反击。
一、血色诏书里的流放者
眉州刺史任上的某个清晨,徐敬业接到了一纸贬谪诏书。朱笔划过的"柳州司马"四个字犹如四道血痕,揭开了武则天清洗李唐旧臣的序幕。

驿站快马送来长安密报:废帝李显被囚房州,宰相裴炎血溅丹墀,紫宸殿上垂帘后的那个女人正在改写大唐的宗庙谱牒。
祖父李勣的画像在祠堂中沉默。这位凌烟阁功臣绝不会想到,自己当年支持武后摄政的决定,竟会让孙子踏上截然相反的道路。
扬州都督府的舆图上,徐敬业的手指重重划过长江天堑,被贬谪的失意文士、遭排挤的关陇将领、心怀李唐的没落贵族,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
二、檄文惊破长安梦
当骆宾王掷笔的刹那,《讨武曌檄》的墨香混着血腥气飘向九州。"一抔之土未干,六尺之孤何托"的诘问,化作刺向武周政权的利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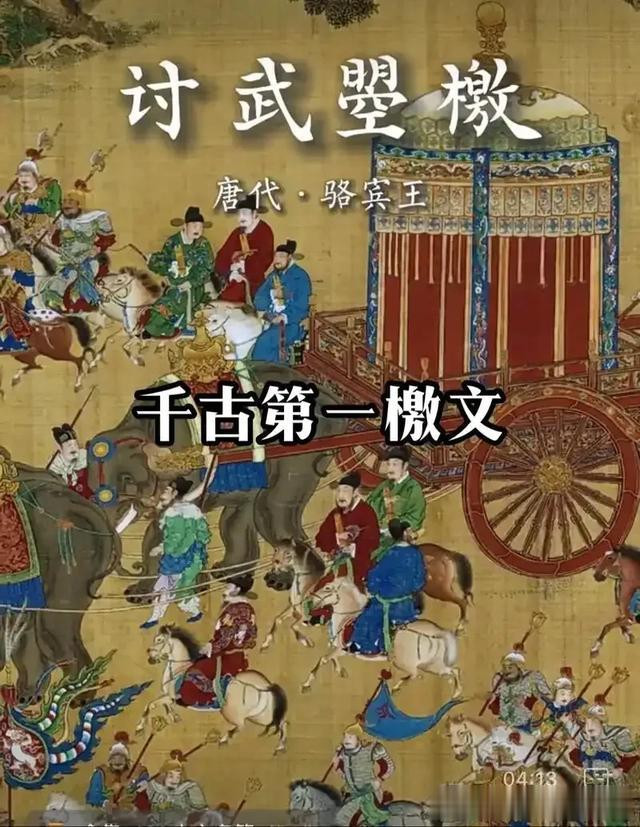
这篇惊世檄文在江南印刷坊被连夜刻版,驿卒们怀揣着滚烫的纸卷奔向各道州县,长江沿岸的城楼上,李唐的赤旗重新招展。
但匡复府的将军们很快发现,那些在酒宴上慷慨陈词的豪强,面对真刀真枪时纷纷退缩。
魏思温建议直取洛阳的战略,被薛仲璋"先取金陵"的保守方案取代。义军在长江南岸的徘徊,给了武则天调兵遣将的喘息之机。当李孝逸三十万大军压境时,楚州城头的匡复旗已在秋雨中褪色。

三、海陵渡的落日余晖
十一月的寒风卷过海陵渡,徐敬业战马的铁蹄在冰面上打滑。身后追兵的箭矢穿透铠甲,这位曾梦想光复李唐的贵族公子,此刻终于看清了门阀政治的残酷真相——扬州豪族的钱粮、江淮文士的笔墨、关陇旧部的刀剑,终究抵不过一个成熟帝国的战争机器。
润州江面上漂浮的义军头盔,映照着武则天在洛阳端门宣布改元"垂拱"的盛况。但徐敬业燃起的烽火并未完全熄灭,六年后琅琊王李冲在博州再举义旗时,扬州城头的血迹还未褪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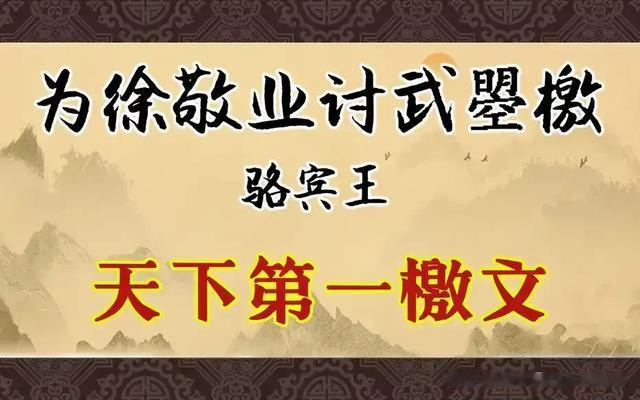
直到神龙元年五王政变,徐敬业未竟的事业才以另一种方式完成,只是那时,大明寺的银杏已黄了二十个春秋。
这场持续六十日的叛乱,像一颗投入历史长河的陨石,激起的涟漪最终改变了河流的走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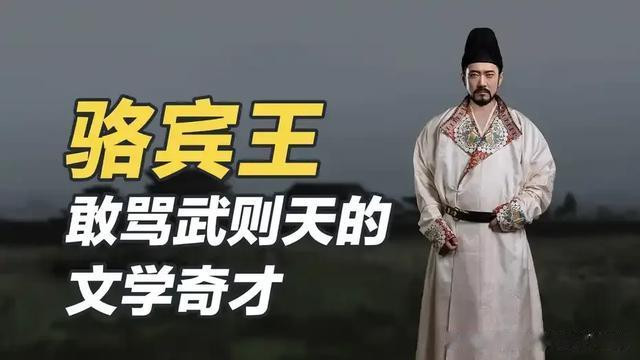
徐敬业的头颅被石灰封存送进洛阳时,他腰间那柄祖传宝剑的龙纹,正在匣中渐渐锈蚀成斑驳的青绿。